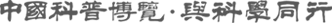首页 >> 演讲专家
缅怀与回忆华罗庚教授
杨乐院士
华罗庚先生在日本逝世时,杨乐院士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当他和他的同事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心情异常沉痛。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今天是6月12号。25年前的今天,有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中国的一代巨星华罗庚教授突然逝世。
1985年6月12日晚上十一、二点了,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夜深人静,显得分外响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居民家庭安装电话的还不多,我下班回家很少有几个电话,晚上九时以后一般不会再有电话铃响,是看书与思考问题的好时光。拿起听筒,是研究所党委书记潘纯同志打来的电话。老潘是位很正派的老干部,然而我们通常只在所内会议上见面与谈话,并没有个人联系。一听到他的声音,我感到可能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并有不详的预感。
然而当我听到他在电话中通报华老当天下午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完学术报告以后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已于晚上十时逝世时,我还是极端惊愕,茫然不知所措。不仅当时如此,而且在随后的几天里,到机场迎接专机运回华老的骨灰盒,以及到八宝山大礼堂参加告别华老的仪式,我一直为这种惊愕与茫然的情绪所笼罩着。当时,《人民日报》曾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章,然而在那些天里,我无法稳定情绪,理好思路,完成这项任务。
我记得还是中学的时候,就听说过华老的事迹,很多同学们有时候谈起在一些报纸上或者期刊上看到介绍华罗庚的非常传奇性的一些事迹。
第一次见到华老,是1956年我进入北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系里请华老来给大家做通俗演讲。
华老讲的非常风趣,很具体,包含的内容也很深刻,其中有些内容我觉得到现在也还能记住。他说,你们要随时随地发现数学问题,比如说一个汽车牌照的号码,这到底是不是素数,或者说这是不是若干个素数的平方和呀,他能提出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到了三年级以后,要分专门化了,那时候有很多领域。但是当时我们中间一批成绩很出色的同学,都向往念函数论,我觉得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华老的影响。我们分到函数论专门化以后,20多个同学还专门跟华老约了,到他在数学所的办公室(原来那个楼中间的412房间)座谈,我们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讲学习函数论的意义和方法,我觉得感到非常亲切。
真正跟华老有比较多的接触是1962年分到数学所以后。那一年,华老招了几个多复变的研究生,都是我们北大的同学。因为我和张广厚是熊先生的研究生,在同一个函数论研究室,所以当华老把他的研究生约来谈学习上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有时候也顺带把我和张广厚叫去。我记得我们刚到所里,他就希望我们打好基础。
我觉得华老对青年人的提携是非常突出的。当我们刚到数学所的时候,就听到他的一些传说。说他在讨论班上要求青年人演讲的时候非常之严谨,不断的提问题,而且问题常常一个程式跟着另外一个程式。到最后有些学生就觉得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称为“挂黑板”。但62年我们到数学所以后,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已经比较少了。可能华老也是开始年龄更大一点,对年轻人更加多的是支持和鼓励。他常常说,我是希望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向上攀登。华老勉励年轻人学习要十分勤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人家花一个钟点做的事情,学的东西,他花两个钟点来做,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家一个钟点做的事情,我20分钟就可以做出来,就因为前面打下了好的基础。
华老当年学习是很勤奋和努力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时候,钱伟长先生曾经到我们院来,约了元老,跟我们谈过一次话。
谈话中,他提到当年在清华学习的时候的事情。他是1931年秋天入学,入学不久,就“九一八”事变了,他原来在中小学阶段读过一段时间的诗书,原想进大学以后学中文和历史,但到学校以后遇上了“九一八”,他就改变了方向改学物理。因为中学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当然遇到很多困难。他说他非常勤奋,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当时他本以为自己是全清华最用功,最刻苦的一个人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还有人比他更用功,他说就是华老,华罗庚。他说自己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但是华老每天早晨四点半就开始学习了。这个例子说明华老当年的勤奋,他也是用这种精神来鼓励年轻人的。
华老还提出来年轻人要学习前人已有的知识,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再提高。他跟我们讲他在清华学习复变函数的事情。他说曾觉得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证明了一些新定理,可继续深入的学习中才发现,他证明那个定理并不是新定理,原来就是个系定理。所以他说要很好地学习前人的东西。如果留在原地的话,他说他不可能有学术上那么高的造就,是得益有清华和剑桥这么好的条件。其实,我觉得他本人的努力是更加主要的。
华老还对我们说,如果年轻人学生向你提问题的时候,要跟学生一起来做。而不是把学生提的问题拿回去,经过晚上的解答,第二天把非常漂亮,非常完整的一个答案来给学生。他说跟学生一起做,学生就发现,原来这个老师或者专家也不是天才,他拿到这个问题以后,也不是一下子脑子里就有了很完整很漂亮的答案,可能一开始也感到惶恐,无处下手,也感到中间可能有曲折,他说种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他说这个让学生要有深切的了解,就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那么愚蠢,遇到这个问题都不会了,老师和专家拿到这个东西以后,也照样的会有遇到曲折,遇到障碍,遇到困难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有媒体宣传我和张广厚。过了不久,华老见到我和张广厚,他跟我们说,他在哈尔滨期间医生和护士问他,说报上宣传的杨乐、张广厚是不是你的学生。他说不是,他们是我的师弟。他说我们有共同的老师熊庆来先生。当然这是华老和对我和张广厚的抬举,也是希望提携我们的一种表现。
1979年3月份,我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中国数学会理事会会议。当时也是刚改革开放不久,浙江省的科协在杭州的一个很大的剧场举行对年轻人的报告会。华老、苏老等人都参加了。
会议前一半由这些老先生做一些简短的讲话。休息以后,会议安排请我做一个关于学习的报告。中间这些老先生退场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华老跟我说,这儿就交给你了,我当时就觉得,华老对年轻人,哪怕那时候到场的实际上主要是一些中学生,都是非常关心的,希望他们好好成长的。
另外,华老对学术交流也非常重视。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华老带一个数学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访问完了,华老又留在那儿继续到一些美国的大学去,一共访问了五个月。回来以后,他就提出来,他说一些文艺表演的团体到国外,或者到外地进行了演出以后,回来要有一个汇报演出。他说我们现在也改革开放几年了,很多人也出过国了,做过学术演讲了,也看到国外的一些情况了,他说我们是不是也来一个汇报演出呢?在他的提议之下,他就约了一些数学界的同仁到中国科技大学。
华老在那儿呆了四个星期(大概是1981年大概春天的时候),他约了王元先生,约了我,张广厚还有数学界的许多学者到那儿去,每个人都做演讲。我记得我做演讲的时候,华老也在场。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听众中间也有比较多的是研究生或者是年轻学者,我希望讲一些他们能够听懂的内容。所以我尽量把演讲内容的程度稍微压低一点。因为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我演讲中举了一个不等式的证明,这个不等式类型有些特别。演讲完了,华老在纸上把这个不等式写下来,而且还琢磨了大概有一个多钟点。他说想知道这个不等式到底是什么含义,而且他还期望能给出一个证明。这就是华老,对学术交流非常严肃和认真。
这些方面的事情还比较多。比如1979年,我到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有一次在走廊里,一位数学系的教授叫住我,他说你认识华罗庚吗?我说当然。他说他是华罗庚教授二十世纪40年代末期在伊利诺依大学当教授的时候的学生。所以他看到我是一个中国学生,他马上就联想起华老来。当然这样的事例还比较多。其实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数学因为经过了二十年的在封闭环境,尤其是文革十年与外界的完全隔绝,在那时候水平不理想,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华老是一个例外。
华老在中国数学的近代史上,我觉得水平是最突出,贡献最大的一位数学家,我们现在纪念他,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现在的绝大多数中青年的学者,可能都没有跟华老接触过。所以我们要宣扬华老的这种对对待数学研究,对待培育年轻人才,对待学术交流的精神,以他为榜样,我们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国际上的数学强国。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今天是6月12号。25年前的今天,有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中国的一代巨星华罗庚教授突然逝世。
1985年6月12日晚上十一、二点了,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夜深人静,显得分外响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居民家庭安装电话的还不多,我下班回家很少有几个电话,晚上九时以后一般不会再有电话铃响,是看书与思考问题的好时光。拿起听筒,是研究所党委书记潘纯同志打来的电话。老潘是位很正派的老干部,然而我们通常只在所内会议上见面与谈话,并没有个人联系。一听到他的声音,我感到可能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并有不详的预感。
然而当我听到他在电话中通报华老当天下午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完学术报告以后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已于晚上十时逝世时,我还是极端惊愕,茫然不知所措。不仅当时如此,而且在随后的几天里,到机场迎接专机运回华老的骨灰盒,以及到八宝山大礼堂参加告别华老的仪式,我一直为这种惊愕与茫然的情绪所笼罩着。当时,《人民日报》曾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章,然而在那些天里,我无法稳定情绪,理好思路,完成这项任务。
我记得还是中学的时候,就听说过华老的事迹,很多同学们有时候谈起在一些报纸上或者期刊上看到介绍华罗庚的非常传奇性的一些事迹。
第一次见到华老,是1956年我进入北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系里请华老来给大家做通俗演讲。
华老讲的非常风趣,很具体,包含的内容也很深刻,其中有些内容我觉得到现在也还能记住。他说,你们要随时随地发现数学问题,比如说一个汽车牌照的号码,这到底是不是素数,或者说这是不是若干个素数的平方和呀,他能提出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到了三年级以后,要分专门化了,那时候有很多领域。但是当时我们中间一批成绩很出色的同学,都向往念函数论,我觉得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华老的影响。我们分到函数论专门化以后,20多个同学还专门跟华老约了,到他在数学所的办公室(原来那个楼中间的412房间)座谈,我们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讲学习函数论的意义和方法,我觉得感到非常亲切。
真正跟华老有比较多的接触是1962年分到数学所以后。那一年,华老招了几个多复变的研究生,都是我们北大的同学。因为我和张广厚是熊先生的研究生,在同一个函数论研究室,所以当华老把他的研究生约来谈学习上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有时候也顺带把我和张广厚叫去。我记得我们刚到所里,他就希望我们打好基础。
我觉得华老对青年人的提携是非常突出的。当我们刚到数学所的时候,就听到他的一些传说。说他在讨论班上要求青年人演讲的时候非常之严谨,不断的提问题,而且问题常常一个程式跟着另外一个程式。到最后有些学生就觉得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称为“挂黑板”。但62年我们到数学所以后,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已经比较少了。可能华老也是开始年龄更大一点,对年轻人更加多的是支持和鼓励。他常常说,我是希望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向上攀登。华老勉励年轻人学习要十分勤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人家花一个钟点做的事情,学的东西,他花两个钟点来做,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家一个钟点做的事情,我20分钟就可以做出来,就因为前面打下了好的基础。
华老当年学习是很勤奋和努力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时候,钱伟长先生曾经到我们院来,约了元老,跟我们谈过一次话。
谈话中,他提到当年在清华学习的时候的事情。他是1931年秋天入学,入学不久,就“九一八”事变了,他原来在中小学阶段读过一段时间的诗书,原想进大学以后学中文和历史,但到学校以后遇上了“九一八”,他就改变了方向改学物理。因为中学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当然遇到很多困难。他说他非常勤奋,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当时他本以为自己是全清华最用功,最刻苦的一个人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还有人比他更用功,他说就是华老,华罗庚。他说自己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但是华老每天早晨四点半就开始学习了。这个例子说明华老当年的勤奋,他也是用这种精神来鼓励年轻人的。
华老还提出来年轻人要学习前人已有的知识,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再提高。他跟我们讲他在清华学习复变函数的事情。他说曾觉得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证明了一些新定理,可继续深入的学习中才发现,他证明那个定理并不是新定理,原来就是个系定理。所以他说要很好地学习前人的东西。如果留在原地的话,他说他不可能有学术上那么高的造就,是得益有清华和剑桥这么好的条件。其实,我觉得他本人的努力是更加主要的。
华老还对我们说,如果年轻人学生向你提问题的时候,要跟学生一起来做。而不是把学生提的问题拿回去,经过晚上的解答,第二天把非常漂亮,非常完整的一个答案来给学生。他说跟学生一起做,学生就发现,原来这个老师或者专家也不是天才,他拿到这个问题以后,也不是一下子脑子里就有了很完整很漂亮的答案,可能一开始也感到惶恐,无处下手,也感到中间可能有曲折,他说种种情况都可能发生,他说这个让学生要有深切的了解,就知道,原来自己并不是那么愚蠢,遇到这个问题都不会了,老师和专家拿到这个东西以后,也照样的会有遇到曲折,遇到障碍,遇到困难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有媒体宣传我和张广厚。过了不久,华老见到我和张广厚,他跟我们说,他在哈尔滨期间医生和护士问他,说报上宣传的杨乐、张广厚是不是你的学生。他说不是,他们是我的师弟。他说我们有共同的老师熊庆来先生。当然这是华老和对我和张广厚的抬举,也是希望提携我们的一种表现。
1979年3月份,我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中国数学会理事会会议。当时也是刚改革开放不久,浙江省的科协在杭州的一个很大的剧场举行对年轻人的报告会。华老、苏老等人都参加了。
会议前一半由这些老先生做一些简短的讲话。休息以后,会议安排请我做一个关于学习的报告。中间这些老先生退场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华老跟我说,这儿就交给你了,我当时就觉得,华老对年轻人,哪怕那时候到场的实际上主要是一些中学生,都是非常关心的,希望他们好好成长的。
另外,华老对学术交流也非常重视。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华老带一个数学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访问完了,华老又留在那儿继续到一些美国的大学去,一共访问了五个月。回来以后,他就提出来,他说一些文艺表演的团体到国外,或者到外地进行了演出以后,回来要有一个汇报演出。他说我们现在也改革开放几年了,很多人也出过国了,做过学术演讲了,也看到国外的一些情况了,他说我们是不是也来一个汇报演出呢?在他的提议之下,他就约了一些数学界的同仁到中国科技大学。
华老在那儿呆了四个星期(大概是1981年大概春天的时候),他约了王元先生,约了我,张广厚还有数学界的许多学者到那儿去,每个人都做演讲。我记得我做演讲的时候,华老也在场。当时改革开放不久,听众中间也有比较多的是研究生或者是年轻学者,我希望讲一些他们能够听懂的内容。所以我尽量把演讲内容的程度稍微压低一点。因为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我演讲中举了一个不等式的证明,这个不等式类型有些特别。演讲完了,华老在纸上把这个不等式写下来,而且还琢磨了大概有一个多钟点。他说想知道这个不等式到底是什么含义,而且他还期望能给出一个证明。这就是华老,对学术交流非常严肃和认真。
这些方面的事情还比较多。比如1979年,我到美国的一个大学访问。有一次在走廊里,一位数学系的教授叫住我,他说你认识华罗庚吗?我说当然。他说他是华罗庚教授二十世纪40年代末期在伊利诺依大学当教授的时候的学生。所以他看到我是一个中国学生,他马上就联想起华老来。当然这样的事例还比较多。其实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数学因为经过了二十年的在封闭环境,尤其是文革十年与外界的完全隔绝,在那时候水平不理想,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华老是一个例外。
华老在中国数学的近代史上,我觉得水平是最突出,贡献最大的一位数学家,我们现在纪念他,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现在的绝大多数中青年的学者,可能都没有跟华老接触过。所以我们要宣扬华老的这种对对待数学研究,对待培育年轻人才,对待学术交流的精神,以他为榜样,我们齐心协力,努力奋斗,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国际上的数学强国。